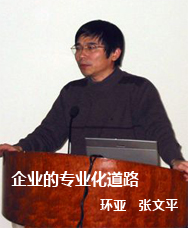
每次采访的路上,我都会忐忑不安,担心自己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真正体会每个人的思想,担心漏掉某一处精髓。这次当然也不例外,我尽量睁大双眼,仔细审视着眼前掠过的“一草一木”,发觉其实“环亚”有着很明显的特质,几乎每扇门上都刻着“攀 pamari”的标志,没顾上细想,便迅速见到了张总。来之前耳闻张总如何“严肃”,如何“苦大仇深”,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平和可亲,满脸笑容的张总,心里的嘀咕一扫而光。为了确保不受打扰,张总特意把我引到会议室,开始了我至今回味起来,依旧温暖、依靠、踏实、睿智、理解、感性、丰富的畅谈。
环亚与模范环亚的关系
张文平:模范环亚公司是我们和法国TNS合资的公司。法国TNS在中国有两个合资公司:与央视有一个合资,是做收视率调查的;与环亚有一个合资,是做专项调查的。
过去咨询服务业是不允许独资的,国外的一些调查咨询公司想进入中国市场,要么就成立一个办事处。因为办事处的功能限制的很死,所以开展业务就会受到影响,只能走合资的道路。外资公司为了保持它自己在经营上的独立性或者自主性强一些,合资时他们希望自己控股,自己来经营管理,这是前提。主要合资的框架是模范环亚这个合资公司,我们不参于经营,但在业务上进行合作。
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合资进入中国市场,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合作可以在它身上学很多东西,包括对我们人员有一部分培训;从它身上获得一些业务,当然还有一部分管理费。
环亚与模范环亚是分开的,独立经营。
企业经营好坏主要是管理,而不仅是体制问题
张文平:环亚到现在还是国有公司。实际上体制改革我们也是一直在推进,这个改革变化不是简单的,我想有几个因素制约它。
第一,由于北京是首都,事业单位改革在北京市是比较慢的,因为我们上级是事业单位,如果上级不改,我们就不好改。这里面牵扯到政策问题,从92年成立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有一部分人一直做到现在,牵扯到对他们身份的一些转变,需要有一些政策,这些政策目前还很难到位,我想这是宏观上和客观上的制约;
第二,我想也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改制其实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要达到一个目的,有很多很多手段,就象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有很多路可走一样。也许改制是一条捷径?但是很难判断。可能对于这个企业是捷径,对于另一个企业就不是捷径。我研究了国内的许多企业的改制过程和结果,我觉得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主要是管理,而不是体制的问题。为什么改制?如果改制是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那也许应该认真研究实施;如果是为了股权的问题,那就是利益再分配,成功的很少,实际上改一个东西比新创造一个要难的多。
第三,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经营环境也不规范,我认为在当前这样的背景下,从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考虑,国有背景有一定的作用。虽然它是一个双刃箭,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但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但是当前还是利大于弊。
一说国有体制,大家都说吃大锅饭,其实,国有体制也可以不吃大锅饭,私有企业也可以吃大锅饭呀,它不是体制带来大锅饭的问题,是管理的问题。管理决定要吃大锅饭那就吃大锅饭,管理上不想吃大锅饭就不吃大锅饭。
环亚改制构想
张文平:环亚的改制,一定要启动,而且已经在进行。在股权分配方面,我们会分几个层面,这也是总结很多企业的改制得出的经验。有的企业改制的时候全民持股,全民持股我认为就是新的形式下的大锅饭和新的形式上的一种奖金分配体制。全民持股其实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我想我们可能会将股权分三个层面。不是强制、强迫的是自愿的。一方面是管理层持股,可能占的比例稍微大一些,从总体上来说管理层起码应该是控股;第二个是关键岗位,关键岗位员工持股;第三个是员工,就是有忠诚度的或者是喜欢、热爱这个企业的,可以长期做下去的员工,自愿持股。
外经贸委的背景使我较早的进入了市场研究领域
张文平:我85年初进入北京市经贸委国际贸易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所是在84年成立,主要是为政府提供一些有关信息、政策等方面的服务,是市政府所属的一个事业单位,主要为了政府服务。当时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刚开始,许多国外大的企业、公司或者机构都对中国市场感兴趣,它们要进入中国市场。而进入中国市场按它们在国外的习惯做法,肯定要做很多调查和研究,关于投资政策、市场、环境等很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当时国内根本没有调查公司,外商没办法就找政府,而政府当时规定的对外的机构和部门就是外经贸委。外经贸委更多的事情是管理和制定政策,不可能对外商不断提供这些咨询与服务,只有把这个研究所介绍给外商了。开始的时候更多的研究属于行业研究,研究消费者少一些,更多的研究投资环境,因为我们刚刚改革开放,国外的一些厂商还没有在中国设厂,设厂前的一些关于投资环境等战略上的研究是他们急需的。
妮维雅――记忆中的第一单
张文平:我记得最早接到的产品调查好像是妮维雅,大概是86年,做入户调查。那是我第一次做,从来没有接触过,噢,原来国外的一些厂商还是那么关注用户。接下来就陆陆续续一直在做,到92年,事业单位的改制,就在原来我们贸研所咨询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环亚公司。
不是企业家也不是专家
张文平: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包括我本人,我觉得到目前来说还不能说自己是企业家。因为进这个领域的时候,是从一个专业人员进入的,是做一个具体研究工作的,是这么做起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行业,我认为本土公司很难不大。
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专家也算不上,企业家也算不上,那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有几个特点:
第一,现在算起来20多年了,傻子也能悟出点什么来了吧,经验的积累。
第二,我好象天生对这个市场相对比较敏感,这个我也说不上什么道理来。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比如当我们分析一些问题卡壳的时候,想解决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隐约有一些灵感,这可能跟经验的积累有关吧。
“项目式”管理到“矩阵化”管理
张文平:矩阵化管理是我们通过不断摸索、探讨的后,开始实行的。开始的时候人不多,属于项目式管理,来一个项目,公司里人一起上,咱们一起干,干完以后再分奖金等等,随着发展成立了部门,按流程设计部门,搞流水作业,研究部、客户部、数据部、实施部等等。到今天我认为现在的矩阵化管理模式跟我们公司的业务定位和我们公司的发展是相协调的。
从管理角度来讲,公司高层有总经理,有四个副总经理,其中,一个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整体营销,一个副总经理负责公司内部的业务管理;一个副总经理是负责公司的人、财、物的管理,这是横向的。从纵向上,有一个副总经理专门负责汽车市场研究领域;有一副总经理专门负责行业行业研究领域;还有一个副总经理专门负责快速消费品研究领域。
四大事业部
张文平:我们现在的业务定位主要在几个方向上,从事业部角度来讲,有一个汽车研究事业部,有一个行业研究事业部,有一个快速消费品研究事业部,还有一个专项事业部,一共是四个大部门,表面上这四个大部门的范围挺广,但实际上进一步定位就比较专了,比如汽车研究事业部里面,我们可能偏重于商业用车更多一些;在快速消费品方面,可能偏重于洗涤用品更多一些;在行业研究里面我们偏重于公用事业和化工建材方面更多一些。专项事业部指的是专门为一个客户服务,那就是全面性的和连续性的项目,专门成立一个部门。
“靠我们大家努力,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好”
张文平:我非常同意李思的那翻话,“做大不等于做强,做长才是做强”。其实我们公司的经营理念很简单,只要达到这个目标不管公司大还是小,就是“靠我们大家努力,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好”!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宗旨,很实际的,要求没那么高,这就是我们公司想做的事情。对外我们肯定是照章纳税了,承担一个企业应该对社会承担一些义务,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就靠大家的努力,使我们每个人生活更好。什么样的平台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就创造什么样的平台,最大是不是好,大和小是对资源而言的,你本身的资源不足以承受很大的,老想做大的就会走偏路了。
同一级别最应该吃“大锅饭”
张文平:我们现在的分配体制也是从奖金、提成等等走到今天,我们实行了一种现代企业分配制度,就是岗位工资。岗位工资就是你有活没活都能拿到工资,但是定位你工资的时候有一个考核过程,我们现在实行两个体系。
专业研究人员走研究体系,我们分研究员和研究经理这两个级别,研究员有6个档次,研究经理有6个档次。我们每半年都会有一次考核机会,理论上讲一个人在“环亚”连续工作6年的话,他都会每半年有一次晋升机会,一共十二次机会,6年他都会有机会的,这是一个体系。竞争是一定的,不可能每人都会晋升。
另一个体系是管理岗位,实行管理体系。我们从部门经理,到助理/总监再到副总、总经理这个级别,一共四个级别,也是每个级别有6个档次。从总的分配原则来讲,应该这么说,如果公司经营的不好,研究人员的工资不会受影响,就是专业人员的工资不会受影响,我们的研究经理可能会超过部门经理,如果公司经营好的话,那部门经理肯定会超过研究经理。专业研究人员只承担工作责任,管理人员同时要承担经营责任。
同一级别基本没有差别,不同级别有差距。同层应该吃“大锅饭”。比如在企业里,我们俩各方面都一样的时候,分配不一样,那是你企业的问题,是企业的资源分配有问题。
没有分公司
张文平:我们没有分公司。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建立。首先分析为什么要设点在这个城市,设点的目的是什么。过去,客户不太明白,你去告诉客户我在全国各个省市都有点儿,客户才信你,现在客户都是跟着项目走,你到一个地方设了一个点,所有的点你都找一个人而且办公室都没有,或者有一个办公室就三个人,你可以对比一下,是你有一个办公室就三个人的实施力量强呢?还是当地的一个二十人的公司实施力量强?所以成立分公司的前提是你想干什么,是开拓当地的市场还是只做实施,这两个目的,或者这两个目的加在一起。大家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目的,只做当地的实施,只做当地实施的时候你不可能弄一个庞大的队伍,只做实施,没有那么大的业务量,也投入不起;紧接着,第二个目的——除了实施还做当地研究,逐渐做着做着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公司了,很多这样的例子。这跟我们文化是相关的,就是当这个公司不具备能力的时候,他很靠这个母公司,当他具备能力的时候他就要脱离,我认为这种独立是一个必然,不是一个人的品德问题,跟品德没有关系,这是必然,与人长大了总要离开家的道理是一样的。
到国际同行会议上学习
张文平:起步的时候,人才的培养主要依赖于模范环亚,当时还送到香港去培训。从97年以后培训全靠自己。在培训上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从92年开始成立这个公司,应该说我们是比较早的就把眼光投入到国外,像ESOMAR,我们在94就参加了,那时国内相当多的企业还不知道。前几次参加大会,别说中国人,亚太地区的人都没有,随后逐渐的有了,逐渐的中国人就多起来了,后来在土耳其会上一共有五十几个人,其中有二十几个人是咱们中国去的。95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参加国际上的会议,每年都会参加,主要是业务骨干去参加,甚至有刚毕业一年的。从95年开始,我们大概有不下二十人次参加过这样的会议。
人员流动,心里很难受
张文平:参加过培训的人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流动了。当初送他们学习的时候是想给他们创造机会,得到锻炼,没想他们学完以后会流动。出现这种情况非常非常难受,很痛苦。因为我们公司在人员方面不像其他一些公司,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这个,我们从来也没开过人,现在也是这样。99年以前还只有进没有出,非常非常稳定。2000年到2001年流动非常大,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是当时大的社会环境,IT业发展也很快,大量招人,整个社会,人都在躁动,这是一个大的社会环境。
第二个是公司,从92年成立到2000年将近八年的时间积累了很多很多问题,问题到了极限。我们当时有七个都是大学毕业后,在这儿工作了五、六年,陆陆续续的走了,走的结果好象是一种必然,但是这个过程很痛苦。有很多出国的,到国外上学去了、找工作了,还有的是到客户那边去了,到大的公司里去了,基本上都是去的外企。因为企业平台有限,又很难满足个人的发展需求,他们陆陆续续的都走了。他们要走的时候,我都做工作,跟他们父母去谈,因为我们跟他们的父母关系都非常好,公司以前经常组织一些活动,家庭联谊会,因为晚上老加班,父母都很担心老加班太累,我们到半年的时候就请父母吃饭,找个最好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很熟。家长都不同意他们走,但是还是没有留住,当初我非常非常难受,这是2000年的事情,后来就走走进进,我记得99年的时候,那一年一下子走了三个进了八个,这八个人到今天还留下三个,有五个人其中四个是出国了,现在这三个人在这儿工作了六个年头。我回过头来看,这是种必然。
非典到现在研究人员没有走的
张文平:我们现在招人已经是固定的程序,因为我们现在有专人在做,她会随时把握这些岗位的变化,从非典到现在研究人员没有流动的、没有走的。我对现在公司的人力资源结构比较满意,人员的结构、能力和制度也比较好,刚才我谈到了三个业务副总,三个业务副总有一个从92年就开始一起来做;还有一个副总他是大学毕业在这工作了六年,期间又攻读了MBA;还有一个副总是去年聘来的一个留学的,出国以前在欧共体的国内机构工作过,学完以后在国外的公司工作了两年;还有有两个助理也是在这里工作了六年,还有一个行业部门的经理是从我们研究所原来做政府课题过来的,也是从业七八年了,还有两个部门的经理是工作五年了,在我们公司里面起码有八个人是相当有分量的。
进门的时候看学历,进来以后就再不看学历
张文平:在人员的管理上,我们进人的时候看学历,工作待遇会不一样,比如有的是研究生、有的是博士、有的是大学本科生。但第一年以后,开始考评的时候,就跟学历没有关系了,看能力。
别说“他拿多少,我就该拿多少”
张文平:公司提倡的是,如果对你的工资不满意,可以跟我们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任何一个管理者去谈,但是首先你应该怎么谈,如果谈:我干了多少活,我认为我的能力怎么怎么样,这种谈话我们非常欢迎,马上会组织来考评、来测试;但是如果要谈他怎么拿那么多,我怎么拿这么低,那对不起,你别跟我谈。他拿多少跟你拿多少没有关系,不是说他拿多少你就应该拿多少,你的工资你自己满意不满意是根据你的付出和你的能力,而他是根据他的。这套理念在公司里不断的强化,目前为止见到了效果。
更人性化的管理
张文平:咱们这一行业里面女孩子比较多,结婚以后,有小孩的过程中,有很多公司在歇假的日子里没有钱,歇假完再找工作。我们公司就有一套关于生小孩期间给她一年假,一年里面给她相对还不算低的工资的方法。再比如,虽然我们公司上班也打卡,但我们主要是对行政人员,对我们业务人员来讲相对宽松很多。
没有人因为工资降低而离开
张文平:在SARS期间我们也面临着裁员问题。SARS前,我们的业务非常好,签的大单子很多。由于都是大单,大单的付款是分期的,启动费很少,分二期付款、三期付款、四期付款,更多的利润是在后面,公司签了好几个大项目,前期投入很大,把公司原来积累全投进去了,结果遇上非典,说不能干马上就不能干了,项目停了,钱进不来,发工资都成问题了。怎么办,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裁员、一个是降工资。围在一起我们开会,开职工大会,到底采取哪个方法,大家一起出主意,后来大家达成了共识——选择降工资。降钱的时候降的幅度不同,高管本来工资就高,所以降的多一些,普通员工本来工资就少,所以就降的少一些。没有人因为工资降了就走了的。我认为,SARS问题,不是市场上做生意的问题,是人类面对自然灾难,这时候,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是不是“家”?
张文平:企业到底是不是员工的家?开始是绝对的家,后来又绝对不是家。现在是另一种概念。要说企业一定是职工的家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企业跟职工一点关系没有,也经营不好,这个度不好把握。这个度要结合不同的企业性质、不同的企业人力资源结构,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没有一个统一尺度。但是这个企业资源结构的形成和管理层的组成,和这个老板是直接相关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企业过去是家,应该是从99年之后,家就越来越淡化了。现在,我们正在尝试建立一种新型的符合自身特点的“家”。
企业的专业化道路――调查公司、研究公司和咨询公司
张文平:我们企业现在已经进入了专业化的轨道,是专业化深入的问题,这也是整个行业在讨论的问题,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公司在转向在做咨询,我对这个是有看法的。我觉得研究公司和咨询公司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不是你改个牌子就可以叫咨询公司了。变成了咨询公司,就需要调整整个的人力资源,我们国家为什么有很多咨询公司做的不好,或者做“一锤子”买卖的原因,就是不具备做咨询的能力。
我是这么一个概念,我认为这是一个产业链。先是调查公司,后是研究公司,再有是咨询公司。
其实我们国内相当多的公司是处在调查公司这个水平上,调查公司是把现象向客户描述清楚,调查公司应该面对成熟的客户,象宝洁等等。就是你把数据提供给他你就完成任务了,成熟的客户具有这个能力,最早的时候我们国内是调查公司,是什么原因,因为最早的时候市场需求主要是跨国公司,是成熟的公司,所以,我们最早服务跨国公司,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一个特点。
随着国内的企业和随着客户群的扩大,对调查公司的需求就不同了,原来你给他提供的调查数据不够了,因为他本身不成熟,他就逼着你向研究公司这个方向发展,我认为研究公司是要告诉他是怎么回事,同时还要告诉他为什么。
而咨询公司告诉他怎么办,这是咨询公司要做的。我举一个例子,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病,但是我问你什么你都不告诉我,我问你有钱吗,你家住什么地方呀,你说这个保密。那我给你下处方的时候就无法下了,在我不了解你的基本情况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你去美国治病吧,结果你骂我一顿。因为你连去卫生所都去不起,还能去美国治病吗?
调查公司、研究公司给客户提供的建议经常有这么一种情况,客户说你给我提供的意见根本没用,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什么原因?因为客户的内部资源不向研究公司开放。现在我们做市场调查的时候,客户只让你了解外部资源,而仅仅了解外部资源你就无法提供建议。而咨询公司呢,客户是把内部资源向咨询公司公开的,有了内部资源再结合着外部资源,这时候提出的建议那才叫建议,而我们这些调查公司、研究公司提出的建议那不叫建议,那叫理论。
客户为什么向咨询公司开放他的内部资源,因为咨询公司跟客户讲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力资源结构,我是什么样的专家,客户一听,对。而调查公司不具备这样的人,客户永远不会给你提供他的内部资源。那怎么办呢?我想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从调查公司进入到研究公司,而把研究公司要做足,就是把外部资源分析的非常透彻,我给你五套方案可选择,你去选择,自己去结合你自己的资源去选择,或者你把你有效的内部资源公开一下,我再给你五套方案你再选择一下。这就是我们好多公司想改为咨询公司所在的问题,不是改个咨询就改了,因为你的人力资源结构当时就不是这样的结构,包括你此时的技术,你只是知道外部的东西,关于企业内部的东西却不清楚。
不会往咨询方面发展
张文平:我们不会往咨询方面发展。要改一个公司是发展战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套方法和一个团队的问题。我们不会轻易往咨询这个方面转。我想我们需要再把研究做透做深,这种研究一定要做的很深。比如简单举一例,过去做一个研究,说某个政策会对市场产生影响,这样这么一句话,对客户来说不痛不痒,那你能做到什么,这是政策的影响能不能定量,对手机到底影响多大的份额,你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你的附加值就高了。比如满意度有很多指标,这么多指标先改进那一个,通过各种方法,把重要程度排出来了,哪个最重要就改进那一个,客户按照你的方法去做了,做完后,有的地方管用,有的地方就没太管用,那客户评价你这份调查是不是有点问题。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时候,认为不是我们的调查有问题,是我们研究的深度不够,因为我们中国太大了,差异性很大,可能东北和西北人对事物评价的重要程度不一样,比如北京人更看重时间,而山西人更看重价格,所以在山西省做一个项目,你更多的要考虑价格问题,而在北京要考虑时间问题,你不能说全国统一就考虑时间,要有差异性。给客户考虑到这种程度,你的这种深度研究就到位了。我想调查公司应该向研究这个方向发展,那从一个产业链的角度来讲的话,缺谁都不可,不可能出现调查公司没人做,都去做咨询公司。
市场经济就不应该出现暴利
张文平:行业利润太薄的问题,我觉得心态应该平衡,市场经济就不应该出现暴利。我认为只有两种行业能够有暴利,一个是垄断行业,另一个行业就是毒品。除了这样的行业以外只要是在市场上,只要在市场经济上就不可能有暴利的行业。我们的企业年龄都不是很长,而且都是创业一代的老板,都有一种致富心里,希望尽快的积累财富;另外一点是大的社会环境,因为对近期有把握,对未来预期等,所以要积累财富,如果你对未来有信心的话,你积累财富干什么呀,我们做一个平常人,如果对未来有信心,你还积累财富干嘛?我不光不积累财富,我还要今天花明天的钱,但是所有的环境都要你积累财富。
不可能通过“关系”拉项目
张文平:现在大、小项目都是投标,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已经比以前改变了,应该相对比较好了,不象原来那种靠关系。我认为现在靠三个东西才能够中标,而关系是第三位的。我认为第一位的是你公司的能力、整体实力,第二个是服务,服务包括价格和时间,第三个才是关系,才能够把这个标拿下来。
最喜欢的人
张文平:那是年轻人考虑的事了
最喜欢的书
张文平:哲学、武侠小说,金庸的尤其喜欢
最喜欢做的事
张文平:工作,上网打桥牌
后记:
采访结束,已经过了午饭的时间,张总亲自送我到电梯口,直至我坐上电梯。温暖之余,更加体会了他对员工的那份关爱、呵护,理解了为什么一封家长信,可以感动更多的孩子。
张总是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作为个人、作为环亚对于协会的关爱都是尽心尽力的。在协会最艰难的时期,曾经帮助协会外请专家组织定性培训;并主要参与《市场操作手册》问世工作。正如张总自己所言:“做为一个中国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好,因为要在这个地方生存,只有生存的环境好了,自己才能更好。作为行业中人,如果我们整个市场研究行业不形成气候、政府不重视、行业本身没有自律、内部松散,那就有一天没一天,有今天没有明天。”
张总说只有工作才是他最大的快乐!工作并快乐着!
本文根据被访者原话录音整理,观点与叙事与本站无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