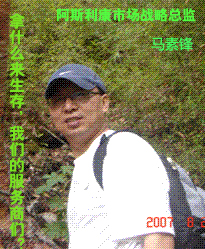
认识Frank是个偶然,约他聊天更是意料之外,可以跟他畅谈3个多小时亦是难得的机缘,而接下来的交流和沟通,终于有了我们第一届医药峰会,为我们行业与医药界最广泛、最亲密的接触拉开了崭新的序幕,在此我们衷心感谢Frank,感谢他的医药同行们付出的所有努力!
绝佳的机遇,事业的幸运
Frank:我在国内读的是天津大学的自动化工程专业,毕业后在国家计委工作了三年后去美国伊历诺易大学商学院读了市场博士,后来在芝加哥的普华永道做了几年的市场战略咨询,之后就转入到这个行业。一开始我在葛兰素史克,主要负责整个公司销售队伍的整合和市场资源的配置等战略规划方面工作,后来转到阿斯利康只负责一个产品,叫思瑞康,我们所做的所有战略决策、信息支持,都只针对思瑞康一个产品。我去的时候这个产品大概一年只有14亿美金,走的时候大概达到了30亿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产品,队伍很庞大,市场部总共有40多个人,我们做信息战略、分析、市场调研的大概有9个人,一年我们有1800万美金的预算,就为这一个产品服务。
做思瑞康的这几年,我觉得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获利最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就是资源,你想支持一个产品,从做市场调研来讲,一年1800万美金的预算,基本上所有我关心的问题都可以从各个角度去做不同的研究、不同的分析,把每一件事看得很透。我交了很多学费,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学的东西特别多,尤其是经验。所谓做这样的一个决策支持,在信息的获得、分析,包括最后的结果,对你做业务决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好的、坏的,结果又会怎样,我基本上都看到了,所以说这是我最幸运的几年,大概没有谁能在职业生涯里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让你试,而且允许你失败,甚至允许你失败两次、三次,但到最后你要拿出对这个产品有意义的东西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幸运的,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试验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过程对我特别有帮助。
从一个到二十个的转变
Frank:做了三年之后,我就想回到中国,现在在阿斯利康,我做同样的事情,阿斯利康在中国市场的信息采集、分析、决策支持、市场调研都由我的部门来负责,只是原来我只负责支持一个产品,现在要负责十几个,还会涉及到更多高层之间、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但基本的工作性质是差不多的。
唯一最大的转变就是我对这些产品的了解,因为医药市场每一个产品都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病,不同类型的病人,不同类型的医生,你对不同市场都需要加深了解。我觉得对我的好处就是,我已经在医药界做了十年了,拿一个新药过来要我了解这个市场,这件事我觉得变得很容易,实际上因为你在整个所谓市场、营销、决策过程中,你的角色很固定,拿我来讲,我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整个高层管理团队的咨询,这就是我职责范围中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对内就是一个咨询工作,这实际上也就蛮简单的,因为咨询本身就是接什么项目,做什么事,你要永远保证你能够给人家拿得出东西来,所以我觉得一个产品到20个产品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转变,只不过需要接触的人多了,需要讨论的事情也多了,但都是做一个项目,就像原来只为宝洁一家公司服务,现在要为很多公司服务,可能变得更忙,但别的没有太大区别。
安全 → 有效 → 安全
Frank:今天行业里的这些人回头再看,一般都会提到耐信,在医药产品史上这是一个很成功很成功的决策,而且对阿斯利康来讲,意义深远。但对整个阿斯利康公司来讲,这几年贡献最大的是思瑞康。
思瑞康那几年做得特别好的还是真正的精耕细作。思瑞康是抗精神分裂症的,本来市场就不大,在一开始做的时候思瑞康强调产品的安全性,但是医生一般说用一个药先要有效然后再安全,所以一开始都没有做好。在2002年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安全性不可以强调太多,因此我们调整了整个产品的定位、宣传,从强调安全性到强调有效性,在有效性方面我更强调它的长期有效。因为精神病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病,只能依靠控制,长期的概念在这里更加重要。从02年开始,整个的产品的宣传全改到长期有效,然后在长期有效的过程中,对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诉求,比如在美国精神病人60%是妇女,所以在美国我们特别强调药效对体重影响很小,但对神经控制会很有影响。基本上在宣传方面我们往一个方向就是说,思瑞康可以使你做一个正常人,从02年开始进入到这个方向,到03年初效果就特别不一样,销售开始往上走。在03年下半年,这个信息做了一年多效果觉得很明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转过来做用量。药一定要用到量才会有作用,思瑞康最小药量是25毫克,有医生最大一天可以吃1500毫克,所以好多医生就停留在300毫克一天,效果就不明显。我们专门做试验得出一天600毫克是目标剂量,效果最好。而2003年以前平均下来,每个病人基本上是每天只有230毫克。从03年开始我们都是推剂量,到05年初每个病人就推到500毫克,效果很明显。在这个过程中,正好赶上04年、05年,药的安全性事件在美国炒得很凶,后来所有的医生最关心的都是安全,这时候回过头来说,当初思瑞康上市的时候,我们认为不太有效错误的信息,安全性,现在成了一个最大的优势。当初思瑞康连做了四年安全性,所有的医生都认为脑子里就是思瑞康最安全,但是对销售没有促进作用不大,所以我们花时间来讲思瑞康长期稳定有效。在这种大环境下,思瑞康安全已经深深地印在医生脑子里了,这时候他关心安全性,首选药就是思瑞康了。
方向的转变
Frank:2003年我们才18个亿,可到了05年达到了25个亿,06年就有30个亿了。思瑞康在这样小的一个市场里,仍然能够有每年30%的增长,是因为理解了医生,理解了病人,要定好自己的定位,用有效的信息来做市场。2005年的时候,我们的销售力量有600人,但精神病院市场越来越小,因为医院就是这么多,再怎么做也就是这么多病人,必定会受到限制。后来我们更多地进行了探讨,能不能往外走。在美国家庭医生什么病都可以看。于是我们就从病人的立场出发,研究病人治疗的过程会是怎样,一般人一定是先找他的家庭医生问这个情况怎么办,家庭医生一般都会先开药,让病人先回去吃药,这个过程一般要持续半年时间,然后家庭医生才会觉得病人应该找精神科医生来看了,这时精神科医生才会接手。所以一般来讲,从病人有发病迹象,而且是精神分裂症发病迹象开始,平均半年时间,才会到精神科医生那里。我们原来做的就是针对精神科医生,所以我们应该往前走。在发病迹象出现的最初半年里,因为很多家庭医生没有经验,一般都会给病人吃治疗忧郁症的药,但对于精神病来讲,这半年最怕的就是这个,特别是精神病中有一类是所谓双性的病人,即有时躁狂,有时忧郁,单给他吃忧郁症的药,会促使他躁狂发作更频繁,更具危害性,当转到精神科时,这类病人的病情一般更严重。就是说家庭医生在精神病这块误诊率极高,这是我们进行市场调研后的结论。这时候思瑞康要想再增长,一定要往家庭医生这边走。
1000个销售代表投入新领域
Frank:为了走向家庭医生市场,我们跟公司提出来要增加销售代表。在美国加一个销售代表是不得了的事,一个销售代表会涉及到整个公司销售结构、人员配置、地区分布,整个大的决策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对前期所有过程以及未来思瑞康继续增长的空间,以及对病人的分布,整个一套分析下来,我们当时向公司提出来销售代表数量要翻倍。这是不得了的数字。公司就要我们证明为什么应该投资这个。所以我们用半年时间,从各方面论证在思瑞康增加销售代表是值得的。我们给公司做出来的预测是增加销售代表的预测,公司第一年一定会亏,虽然会挣一些钱,但是公司一定赔八千万,第二年公司会收回投资,第三年后公司做到2010年的时候应该有25亿回报。最后这个预算做完到最后批下来,实际上公司给了我们的销售资源比我们要求的还要多。
这样一来,实际上把思瑞康整个的过程,由原来对精神科医生探讨精神科专业问题,变成了现在对一般家庭医生教育精神科问题,有什么样的迹象应该用什么样的药。所以整个的定位、信息、材料都不一样了,销售代表介绍的方法也都不一样,所以又是精耕细作准备了大概一年,在2004年底推出来。到现在,思瑞康在精神科,大概占整个市场份额在24~25%左右,在所谓家庭医生这块市场是最大的,大部分病人都在这,在这个领域思瑞康已经做到了60%多,完全占领了这个市场,这个市场有多大呢?实际上算下来,我们当时估计大概能有140多亿的生意,但是中间有好多的所谓忧郁症的生意,实际上真正到我们这里,可能有那么20多亿,30亿的样子。
中美投资预算差异
Frank:思瑞康当时的决策对公司影响深远,所以后来又投资做试验,看忧郁症这个市场是不是可以拿到。公司在05年底做这个决策,投资四亿,这使得思瑞康在全球所有医药历史上,成了唯一一个已经上市六年还会去投几亿美金做研发的产品。投资之后,我们看到后面的市场真的是太大了,思瑞康现在的产品定位是最最理想的,上面精神分裂症这块市场已经吃掉了,现在要再吃忧郁症这块,市场又是这么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思瑞康这三年,是整个职业生涯中做得最开心,最有意思,可能也是最辉煌的几年。同时,我也学到很多东西。我经常会说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找个人过来把问题讲一讲,花些钱做一个研究,拿过报告一看,跟我想得完全不一样,但可以帮助你理解为什么,就接着想下一个问题。我不用去担心老板会不会说钱白花了,你干什么吃的,从来没有,那时候真的就敢这样去试。其实现在回头想想,三年下来很多资源是浪费的。但是我觉得很值,一个是我自己学到东西,另一个是很多疑问得以解决,实际上这也是对整个决策的准备。好多东西都已经过滤掉,坏的结果也都考虑得到,不明白的问题,研究之后,起码知道跟我想得不一样,尽管结果没法用,但起码知道原来想法是不对的,那就接着往前走。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重要,对我今天也是影响很大。在中国我做的事情基本上都一样,每一个产品对我来讲都要考虑到怎么定位,产品市场是什么样,以后该朝哪个方向去发展,已有的信息和了解也都差不多。我要选择什么事情可以试,什么事情不可以试,每一件事情都是说怎么可以花最少的钱把问题解决,我一定是对公司负责,对自己负责,对产品负责。
中国医药咨询行业的困扰
Frank:我觉得在中国最让我困扰的就是这个行业我找不到足够好的专家能够给我这种帮助。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我要做呼吸的产品,儿科和呼吸专业科的医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方法有哪些不同,药要怎么去推,定位是不是一样,我一般都会要求这种问题。咨询公司找多少个医生问这些问题,然后告诉我这个问题30%的医生说这个,60%的医生说那个,这是没有意义的。咨询公司得帮我教育产品经理说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说明在儿科的定位应该怎么不一样,呼吸科定位应该怎么不一样。我在这个行业很难找不到这样一个能够对我的问题有理解,能够真正做咨询的人,特别是在医药咨询行业极少。过去两年,我每年做很多项目,接触的公司很多,到现在大概我只看到几个人,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事情。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咨询行业。
在公司我是咨询,六个市场部经理我经常都会跟他们每一个人进行沟通,就是现在有什么问题,在想什么事情,这个咨询的过程我自己做,但是如果每一个项目咨询的过程还是我自己做的话,那就没法做了。找市场调研公司帮我把这个所谓的执行做了,执行的概念就是我给你主意,经常是研究公司出一个问卷我们来改,实际上问卷最后都是我们来定,找医生时我还得我帮你找,让我们的销售代表把医生联系给你,你来做,把结果基本的统计给我,最后文章怎么写还得企业来说,这个过程我还是在参与。这个世界上最值钱的是人,是人的专业知识,他的知识才值钱,如果专靠跑腿、打工,很难把价钱做起来。所以说这个行业压价压得厉害,实际上原因不在行业,是在咨询行业,我觉得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价值,大概是我们这个行业要改变的。
回头再看,业界如果没有提供客户想要的质量的服务,这个时候我就说现在真的是没有资格再谈所要的报酬。有一个人自己组了一家公司,跟我们做完一个项目,后面的服务所有人都说好。然后报价过来比MS还高,但是我说行,不谈价,因为我觉得我找不到第二个人了,这个人我不能得罪,变成我得想我不能得罪他,他以后不给我做,我们以后的项目也不好做。所以这时候我们从来不谈价格。
有人说医药行业要求太高,我相信在消费品行业,真的权威的调研也少,另外还牵扯到你对医药行业一定要了解,你对药一定要了解,你对这个病还要了解,你还得了解医生,五官科的医生跟外科的医生完全不一样,你必须了解这么细,再加上病人,得精神病的病人和得心脏病的病人,想法、思路完全不一样,你都要有一个概念,要求会更高,所以我是说,是需要给这个行业一个发展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咨询行业能有什么样的人来做,实际上现在是我们供方的水平赶不上。
没有附加值的咨询服务难以提价
Frank:2006年一年是我们项目一下多出来特别多的一年,我觉得06年做得特别苦,因为我也是刚回来,脑子里面的概念都是美国的守则标准,做一个项目,脑子里就是15万美金,折合过来一百万人民币,可报价只有60万,30万,但是做的过程中收费是不一样的。我在这边仍然在学,这个行业所有的这些收费标准都是什么样。能够很好的做成一个所谓市场调研的问题,说明你对我业务的理解,你的调研是抓住重点,你后面的方法,就会说真的是为解决我这个问题服务。接下来出来的问题你又能怎么回到我的业务问题上来说,我这个调研到最后是解决什么问题,给你指明什么方向,在哪些方面可以做什么事,这是我认为调研最大的价值。如果前面的都得我定,后面的报告我又得走同样的过程,那么调研公司就只剩劳务了。
我真正的花费的概念都有,往上一加,我会给15-30%的利润,看你服务怎么样,再把这个加上去,应该是报价,现在就是在走这个过程。所以06年下半年就是我们的原则,那会儿大概我们跟23家公司走过这个过程,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标准确定了,所有公司也都同意这个标准,实际上现在更多的是在做项目本身怎么做的过程。我最讨厌的就是跟调研公司谈价,因为调研公司是属于咨询的,做事有做事的准则和规则,以及职业操守,价钱上没有多大的水分。在美国做真的是这样,每个项目一报价,价钱从来不是考虑的主要内容,你做这事怎么合作好,这就是我们要的,在这个中间很少有采购部砍价这一说,这是中国特色。
美国医药峰会
Frank:各个地方都有所谓的当地的组织,也会组织一些活动,一般都是找一些大的总裁过去,参加就是奔着这些大名字去的,过去要接触,要谈,要聊。其实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全是制药厂行当的人自己组织起来的协会,每年开一次会,这个更多的是交流,在工作中碰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法,做得好的经验交流。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培养人才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交流,人要流动起来你才会长得快,才会有好人出来做这些事。我不担心人才的流动,因为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不开心,水平再高工作也做不好。如果他真的做得很好,水平特别高,做这个位置完全没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他不开心,他会看到诱惑在外面,终于培养了好人,走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比较公平的。在这方面我真的很开通,这都是你自己的事,跟别人无关紧要,你自己把这些都要安排好了。
争人才大家都是公平竞争,这个过程,不是考验我们,也不是考验市场,是考验自己的眼光,做咨询的如果连这点眼光都没有,到最后做下来一定很难成功。
想生存,你凭什么?
Frank:我的理解,能成为一个医药市场调研专家,大概需要十年的经验,五年在调研公司,五年在医药公司,然后出来可以作为一个的咨询公司,再加上两年熟悉的时间,大概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调研咨询人才,一共是12年的时间。整个外企进入中国才多少时间,十年不到。市场调研公司有1500家我都不敢相信,如果大家都在这一行业里去竞争,想作出品牌,一定得凭什么,一定得有跟别人不同之处。做咨询没有一个人说因为我比他便宜,因为我比它贵,到时候一定凭知识、经验、解决问题的方法、沟通的有效性、服务,这个是最重要的。
行业价格低在你不在我
Frank:公司规定在找调研公司时一定要三家比较,如果都没有特色,我做选择只能依靠价格,谁价格低谁来做,行业价格做得越来越低,这原因在你还是在我?如果有些公司为了拿到我的单子,特地把价格压低,然后在执行方面出问题,这就是考验我的时候,我相信我的判断,我有能力做判断这个人可不可以做。如果我犯了错,那这怪我不怪你,有人愿意受骗,一定怪你受骗,不怪人骗,责任分清,愿打愿挨。有的时候真是这样,项目做得后悔死了,最后只能自己来补,最后学到一件事是以后再也不跟他们合作了。
回过头来说,在价格问题上,我不认为是需方的责任。我们的生存环境都一样,你到最后凭什么生存,我比别的人做这行强在哪,为什么强,我只有强才能做这么大的事。所有竞争公司目标一模一样,你可以要多大的项目,可以要多高的利润,你可以要多高,我知道这些价值。每一个客户一定都是说最优价格,性价比,以最少的价钱拿到最好的东西,同时再好的东西一定要花更多的价钱,这是所谓最最基本的市场学的东西。相信这个,然后你再来看你为什么能做这个价钱,这时候是客户的原因还是你的原因,这市场上一千多家调研公司,到最后你凭什么要高价这种优势获优,你自己没有东西要高价,别人为什么要付?这就是竞争。
中美服务水平的差异
Frank:中国和美国在经营上没什么不同,最大的差别就是服务的水平。在美国,做一个项目我会找三家公司,告诉他们要做一个调研项目,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想解决什么问题。把三份方法拿回来比较,我把产品经理也叫过来,这时候更多的决策是产品经理,因为方法都差不多就要找一个能跟产品经理沟通最好的一家。项目开始的状态是这样,方法论上的问题跟我讲,其他的问题会直接找产品经理,之后一起讨论时,他会过来对所有人解释这个问题做了什么,怎么样,有什么结果,这些结果对产品的每个问题怎么回答,有什么方向,都很清楚,这就是所谓咨询公司。这些人都是咨询行业做了十几年,业界又做了十几年,这种水平的人很多。
回过头来看国内,我可能看到很少几个咨询师能做到这样,这就是整个行业。这样操作起来就变得复杂了,我得充当中间人。我对调研公司的操作干涉特别多,因为我不信任。在美国真的像我说的,那些数据我从来不问,我马上脑子里在集中别的事情,但是我知道那个项目大概这会儿完,我这个问题哪天大概会有答案。但是在中国一个项目进行中间,大概我的人基本上都在那,因为他们有责任,要问你做得对不对,现在有什么反馈,都会跟踪,参与程度特别大,因为得监督。在这个过程中要提高,提高水平最好的方法就是交流,先得要把大家召集起来,把厂家的这些人和调研公司的人放在一起,让你们相互谈,相互看,哪个人水平高,哪个人水平低,哪个人这方面好,大家都有个概念。只有这样做,做到整个咨询行业,大家坐下来谈的更多的是这个市场最近怎么回事,有什么问题,我们咨询行业能够帮业界做什么事,我觉得那样是一个健康的方向,我真的不愿看到的就是大家只谈客户怎么把价压得那么低。我们需要的是和客户坐在一起,理解客户, 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大附加值的服务。
客户的信任
Frank:回款问题我承认是客户责任更大,因为像我们,我这同意付款,发票收到,往那一放,财务一走就要走一个半月。从我这就是说大的项目我会保证,按照我的预算的计划,到这时候把钱付出去,因为我相信我的甲方、乙方会按时给我,这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好多小公司我还真的不敢这样做,因为我不敢保证你还会给我改,你不给我改完了我不敢给你这个钱。所以这就是整个经济环境,在咨询行业是一个信任,相互之间没信任,谁也做不了。在回款问题上根子就是你的客户信不信任你,这是最重要的。
人才交流才能发展
Frank:医药行业需要有一个峰会,因为医药行业跟其他行业特别特别不一样,而且医药行业够大,因为它有它的行业特殊性,有它方法论上的一些具体要求,所以我觉得医药行业应该自己组织一个峰会。因为所有人都关心市场,我的产品,我这些医生,我这些病人,都是这样,而且医药行业的很多管理、操作,都有它的特殊性。
业界都有这个需求,因为所有人都是进步的,都想学,都想看看大家怎么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业界是需求是有的,我认为搞这种活动,要是有足够好的,大的药企全都请得到。我的想法就是说,争取能组织一个医药行业的定期组织,会和各个公司一起谈谈大家想干什么事。我是想集中一件事,从我们的角度来搞一次会,谈的全是厂家关心的问题,厂家面临的问题,跟厂家接触,这样来做。因为这是学习的机会,后面的人只要一看课题,大概都会有人来。活动搞得好,各个公司都会来参加,后来发现一个副产品,就是峰会成了找工作的地方,但是对这个行业来说机会很好,人才交流起来才能发展,这一点我坚信不移。
Frank Ma, Ph.D.
Dr. Frank Ma is Director, Marketing Strategy, at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 (China). At this position, Dr. Ma has been leading AZ’s efforts in collecting all market intelligences, identifying 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providing decision supports to improve AZ’s commercial operation efficiencies in its China operations. Prior to moving back to Shanghai from the USA, Dr. Ma was the brand strategy Director at AstraZeneca and marketing strategy manager at GSK. His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leading the efforts in building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ies, developing sales force sizing and structure, segmentation and targeting, brand positioning and messaging. Before joining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r. Ma had over 4 years experience in marketing strategy consulting at PriceWaterhouseCoopers. He served clients in consumer goods, OTC, and pharmaceuticals, including P&G, Coca-Cola, Pepsi, Phillip Morris, GSK, Novartis, etc. Dr. Ma got his Ph.D. in Marketing Scienc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马素锋博士目前担任阿思利康市场战略总监,负责全公司内、外部信息收集,整理,及分析;寻找发展潜力,以及为公司各级业务决策提供支持。在此之前,马博士在阿思利康美国任斯瑞康产品战略总监,以及葛兰素史克美国市场战略经理。在这些岗位上,马博士在市场及营销战略制定,营销规模和结构优化,销售目标选择及计划制定,以及产品定位、产品信息开发等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进入医药领域之前, 马博士作为高级咨询师为普华永道(芝加哥)服务,客户包括宝洁,可口可乐,诺华,等企业。马素锋1997年自美国伊利诺亦大学获得市场学博士学位。
采访/撰文:刘向清、任东瑾
摩瑞市场研究公司
本文根据被访者原话录音整理,观点与叙事与本站无关。
|

